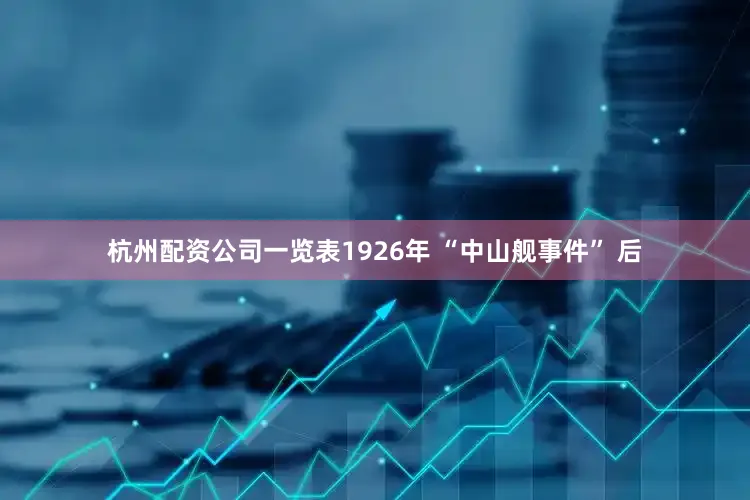
资料来源:中国共产党新闻网《陈赓的戎马一生》、人民网军事频道《陈赓:黄埔三杰之一的传奇将军》
在湖南湘乡出身豪门的陈赓,身边总围绕着几位特殊的人。
这三个看似平凡的人,却与陈赓的命运紧紧缠绕,书写了一段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。
从湘乡老宅到黄埔军校,从起义战场到建国之后,这几人之间藏着怎样的生死抉择与情义坚守?
陈赓出身于湘乡的豪族家庭,其家族在当地声名显赫,拥有大量田产和深厚的家族底蕴。
陈家是武将出身,陈赓的祖父曾是曾国藩湘军的猛将,在当地颇具威望。
在陈赓家中曾有一位名叫卢冬生的牧童。
卢冬生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七都一甲一个佃农家庭,生活困苦。
他比陈赓小5岁,7岁时便到陈家做牧童,与陈赓相识。两人虽身份有别,但常在一起玩耍,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后来陈赓因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而外出当兵,卢冬生则离开陈家,到湘潭十三总老王泰厂当钢行学徒工。
1925年卢冬生到湖南衡阳唐生智部当兵。
1927年春已成为北伐军第八军特务营营长的陈赓,在武汉与卢冬生重逢。
此时的陈赓已是有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,他了解到卢冬生出身贫苦,为人憨厚忠实,便将其调到营部担任警卫员。
在特务营陈赓经常利用出操点名的机会,向战士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,卢冬生深受影响,思想逐渐倾向进步。
那时卢冬生还常随陈赓到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驻地,认识了周恩来等共产党员,进一步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,明白了为人民掌握枪杆子的道理。
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,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,武汉地区局势日益紧张,国民党新军阀何键部甚至将机枪对准陈赓住所,逼迫其交出特务营。
陈赓被迫离开军队,卢冬生则坚定地跟随陈赓来到武昌,后又追随周恩来、陈赓到了南昌,参加了南昌起义。
南昌起义时陈赓担任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六团一营营长,卢冬生任副官。
起义部队南下会昌时,一营冲在最前头,奋勇攻下3个山头,但因友邻部队未能及时支援,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。
激战中陈赓腿部受伤,血流如注。
卢冬生不顾危险,冒着弹雨冲到陈赓身旁,将其抱到山下田沟里,帮他包扎伤口,并在草丛中隐蔽,直到叶挺部队反攻上来,才将陈赓抬到会昌城里。
此后卢冬生一路悉心照顾陈赓。
起义军到达汕头后,陈赓因伤势严重住进医院。汤坑战役失利后,起义军仓促撤出汕头,卢冬生在混乱中四处打听消息,发现情况不对后及时将陈赓藏在一位工人的房间里。
随后他在一位护士的帮助下找了一条小船,踩着淤泥将陈赓推到海中,划着小船送上开往香港的轮船。
抵达香港后他们又遭遇巡捕搜查和刁难,卢冬生始终用身体护着陈赓。
最终在陈赓的建议下,他们躲进厕所暂避,随后卢冬生忍着饥饿,四处奔波,打听到去上海的船讯,将陈赓背上船,顺利抵达上海,找到了党中央。
1927年12月经陈赓介绍,卢冬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与陈赓家相距不到十里的楠竹山村,住着声望显赫的谭氏家族。
湘乡谭氏家族历史悠久,其祖先曾是清朝秀才,家族底蕴深厚。
当时的家族掌门人谭润区,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,他在陈赓将军宅邸附近的七星桥庄园创设了一所学堂,致力于教育事业,不论学生家境贫富,都倾囊相授,深受乡里尊敬。
陈赓与谭氏家族同属湘乡名门望族,两家世代相交,情谊深厚。

陈赓拜入谭润区门下,跟随他学习知识。
在谭润区的教导下,谭政也在私塾中刻苦学习。
谭政比陈赓小3岁,两人同在七里桥谭家祠堂蒙馆读书,因父辈的友谊,他们自幼便情同手足,关系十分要好。
私塾毕业后陈赓考入谭政父亲谭润区执教的东山高小。
而谭政想报考东山高小时,却被父亲拒绝,父亲希望他继续读私塾,掌握正统封建礼法。
无奈之下谭政的父亲请陈赓的父亲陈绍纯收留谭政,陈绍纯欣然答应,谭政便暂居陈赓府中,与陈赓及卢冬生往来密切,三人形影不离。
在此期间陈赓的四妹陈秋葵与谭政也逐渐熟悉起来,陈秋葵自幼与兄长们相处,和谭政可谓青梅竹马。
随着时间推移陈谭两家长辈见谭政与陈秋葵情深意笃,便促成了他们的婚事,谭政成为了陈赓的妹婿。
婚后谭政与陈秋葵一同投身军旅,来到武汉,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特务营任职,谭政担任文书工作。
然而战争年代局势动荡,谭政投身革命后,常年在外征战,与陈秋葵聚少离多。
陈秋葵本就体弱多病,加上对丈夫的思念,身体日益衰弱,最终因病离世。
而谭政则继续坚定地投身革命事业,参与了秋收起义,跟随毛泽东等踏上了井冈山,为中国革命事业不懈奋斗。
1923年冬孙中山麾下的程潜号召青年投身军旅,参与革命事业。陈赓与好友宋希濂响应号召,决定前往广州陆军讲武学校求学。
宋希濂出身豪门,但当时年仅16岁,其父亲不太赞同他从军,宋希濂只好带着三叔所赠的35枚银圆,与陈赓一同前往广州。
一路上得益于陈赓的经济帮助,他们顺利抵达广州,并加入了广州革命政府的陆军讲武学校。
由于学校延期开学,陈赓与宋希濂在闲暇时经常外出漫步。
一次他们来到广州东郊的黄埔岛,恰逢黄埔军校招生,便报名参加考试,最终都成功被录取,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。
在黄埔军校期间,陈赓才华出众,表现突出,与蒋先云、贺衷寒并称为“黄埔三杰”,声名远扬。
蒋介石对陈赓也颇为青睐,曾在其新生花名册下批注“此生貌似文弱,但性格坚强,能吃苦,可带兵” 等字样。毕业后,陈赓留校担任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。
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陈炯明时,在华阳地区遭遇挫折,敌军猛烈追击。
蒋介石担心被叛军俘虏,竟欲拔枪殉国。
关键时刻陈赓迅速夺下蒋介石的手枪,背着他逃离了险境,成功将其救出。
经此一事陈赓更受蒋介石器重,继续担任其侍从副官。
但随着革命形势发展,国共合作出现裂痕。
1926年 “中山舰事件” 后,蒋介石在黄埔学生军中发起 “清党运动”,要求学员严禁 “跨党”,必须 “择一而忠”。
陈赓对此义愤填膺,果断离开了蒋介石阵营,走上了坚定的革命道路。
而宋希濂则选择了不同的道路,加入了国民党,但两人之间的私人情谊并未因此受到影响。
1933年陈赓在上海养伤时不幸被俘,后被押解至南京。
宋希濂得知消息后,心急如焚,立刻召集黄埔一期同学肖赞育、项传远、宣铁吾等十人,联合签名请求蒋介石释放陈赓,并亲自向蒋介石求情,以自己的生命为陈赓担保。
在众人的努力下,蒋介石念及陈赓昔日的救命之恩,将其从监牢转移至客房软禁。

宋希濂担心蒋介石反悔,悄悄向陈赓传递消息,让他不要轻举妄动,并表示会尽力保护他。
后来宋希濂又找机会告知陈赓防守有所松懈,若有机会可趁机逃离,还称愿意为其出具保释,蒋介石应该不会为难众多黄埔同学。
最终宋希濂以劝降陈赓为名,召集众多黄埔同学,假借庆祝陈赓寿辰之机,巧妙安排,帮助陈赓成功逃脱。
蒋介石虽然恼怒,但考虑到诸多因素,并未对宋希濂等人进行追责。
1949年12月19日宋希濂在大渡河畔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,随后被囚禁于重庆白公馆。
一个月后陈赓特意携带两瓶茅台佳酿,前往白公馆看望宋希濂。
当时一同被俘的还有第14兵团中将副司令钟彬,他与陈赓也是黄埔一期同学,重逢时心中难免有些忐忑。
陈赓没有丝毫胜利者的傲慢,他亲自捐资,为看守所筹备了一桌丰盛的佳肴,还邀请了同囚的王陵基上将,一同共进晚餐,席间畅谈往昔情谊。
陈赓没有提及战场的胜负,而是回忆起与黄埔战友们的种种过往,言语中充满了对昔日友情的珍视。
他还特意叮嘱看守所长,要关心宋希濂和钟彬的伤病,对年事已高的王陵基,也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,给予尽可能的照顾。
陈赓的这份豁达与重情重义,让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,王陵基更是羡慕宋希濂和钟彬能有这样一位重情重义的老同学。
卢冬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,革命意志愈发坚定。
1928年初党组织派他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,在中央特科学习情报传递和秘密交通技能。
期间他多次往返于上海与苏区之间,凭借过人的机智和沉稳,成功完成了多次重要文件传递任务,从未出现差错。
当时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曾评价他:“冬生同志虽出身贫苦,但学习能力极强,在隐蔽战线能顶半边天。”
1930年卢冬生奉命前往湘鄂西苏区,担任红二军团警卫营营长。
他将在上海学到的安保经验运用到实际工作中,为军团首长构建了严密的安全防护体系。
在反“围剿” 战斗中,他率警卫营多次击退敌军突袭,确保了军团指挥机关的安全。
贺龙曾在军团会议上表扬:“有冬生在,我睡觉都踏实。”
1934年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师后,卢冬生升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。
在长征途中他率部担任前卫,参与大小战斗数十次。
在贵州松桃战斗中,他身先士卒,带领战士们突破敌军防线,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通道。
战斗中他手臂中弹,却坚持指挥到战斗结束,仅简单包扎便继续行军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卢冬生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。
他克服语言障碍,刻苦钻研军事理论,系统学习了现代战争战略战术。
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,他主动申请加入苏联红军,参与了莫斯科保卫战等战役,在实战中积累了大规模兵团作战经验。
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,卢冬生随苏军回到东北,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松江军区司令员,负责肃清当地日伪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。
在哈尔滨任职期间,卢冬生大力整顿社会治安,建立基层政权,组织群众恢复生产。
他经常深入街道巷弄了解民情,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基本肃清了市区的匪患,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广泛爱戴。
当时哈尔滨流传着这样的民谣:“卢司令,办实事,土匪跑,百姓安。”
谭政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期间,逐渐展现出出色的政治工作才能。

1928年他担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,协助毛泽东开展军队思想政治工作。
在古田会议筹备过程中,他深入基层连队调研,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,为会议决议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毛泽东对他提交的《关于红军内部思想政治状况的报告》十分重视,亲笔在报告上批注了23条修改意见。
1930年谭政任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,主持制定了《红军连队政治工作细则》,对连队思想教育、组织建设、群众工作等作出了明确规定,成为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重要规范文件。
该细则在全军推广后,有效提升了基层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
长征途中谭政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,负责部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整顿工作。
在翻越夹金山时,他带头脱下棉衣分给伤员,自己则穿着单衣行军。
他提出“党员干部先吃苦” 的口号,组织党员成立帮扶小组,确保了部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没有一人掉队。
到达陕北后他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,为培养红军高级政治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抗日战争时期,谭政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,起草了《关于抗日根据地军队政治工作的指示》,明确了敌后战场政治工作的方向和方法。
1944年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》,系统总结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,提出了 “政治工作是军队生命线” 的重要论断,该报告成为全军政治工作的指导性文献,被收录进《毛泽东选集》。
宋希濂在黄埔军校毕业后,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、连长、营长等职,参加了东征、北伐等战役。
1932年“一・二八”事变爆发后,他任第87师261旅旅长,率部开赴上海抗日前线。
在庙行镇战斗中,他亲临前线指挥,与日军展开白刃战,激战三昼夜守住了阵地,部队因此获得“庙行铁军” 的称号。
战后他因战功晋升为第87师副师长。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,宋希濂任第78军军长,率部参加淞沪会战。
在蕴藻浜战斗中他组织敢死队夜袭日军阵地,摧毁日军火力点12处,有效迟滞了日军进攻。
战斗中他腿部被弹片划伤,仍坚持在前线指挥,直到战役结束才去医院治疗。
1938年他调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,驻守河南灵宝,多次击退日军进攻,确保了陇海铁路的畅通。
1941年宋希濂率部参加滇西反攻战役,任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。
在攻打龙陵的战斗中,他制定“围点打援” 战术,先以主力包围龙陵县城,再设伏歼灭日军援军,最终成功收复龙陵,为打通滇缅公路奠定了基础。
此战被纳入国民革命军战史教材,作为山地攻坚的经典战例。
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,宋希濂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,率部参加了多次战役。
1948年他调任华中 “剿匪” 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,驻守湖北宜昌、沙市一带。
期间他曾多次通过秘密渠道了解陈赓的消息,得知陈赓在晋南、豫西战场屡建战功时,常对身边参谋感叹:“陈赓的军事才能,我自愧不如。”

1950年1月宋希濂在重庆白公馆接受改造期间,陈赓再次前往看望。
这次见面两人重点交流了对时局的看法。
陈赓向他介绍了新中国的建设规划,讲述了土地改革、恢复生产等政策。
宋希濂坦诚地说:“过去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,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,才明白你们确实是为人民做事的。”
陈赓鼓励他:“过去的已经过去,希望你能好好学习,将来为国家建设出力。”
在改造期间宋希濂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,撰写了多篇反思文章。
1959年他作为首批特赦人员获得释放,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,负责撰写抗日战争史料。
他撰写的《滇西反攻战纪实》《淞沪会战亲历记》等文章,为研究抗战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。
卢冬生牺牲后陈赓一直牵挂着他的家人。
1950年陈赓派人到湖南湘潭寻找卢冬生的亲属,发现他的母亲和弟弟仍在农村生活,生活困难。
陈赓当即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寄给他们,并联系当地政府为他们安排了工作。
1955年授衔时陈赓在一次会议上特意提到卢冬生:“如果冬生还在,以他的功绩,完全有资格评为大将。”
谭政在建国后历任总政治部主任、国防部副部长等职,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。
他始终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作风,主持制定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》,规范了全军政治工作。
在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,他强调:“政治工作必须结合军事训练和作战任务进行,不能搞形式主义。”
他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。
1956年陈赓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(哈军工)院长,致力于培养国防科技人才。
他亲自制定教学计划,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任教,强调“理工结合、文武兼备” 的办学方针。
在他的主持下,哈军工很快成为国内顶尖的军事科技院校,为我国“两弹一星” 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。
1959年陈赓因长期积劳成疾,住进上海华东医院治疗。
期间宋希濂得知消息后,通过全国政协向医院提出希望前往探望,得到批准。
两人见面时,陈赓虽然身体虚弱,但仍关切地询问宋希濂的工作和生活情况。
宋希濂向他介绍了自己撰写抗战史料的进展,陈赓鼓励他:“这些史料很有价值,要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。”
1961年3月陈赓病情加重,谭政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看望。
两人回忆起在湘乡私塾的往事,谭政感慨地说:“当年在陈家私塾读书时,谁能想到我们会走到今天。”
陈赓握着他的手说:“我们能有今天,靠的是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,要永远记住这一点。”
3月16日陈赓在上海逝世,享年58 岁。
陈赓逝世后宋希濂撰写了《悼念陈赓同学》一文,文中写道:“陈赓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,他的军事才能和高尚品德,永远值得我学习。我们虽政见不同,但友谊长存。”
谭政在追悼会上致悼词,高度评价了陈赓的一生:“陈赓同志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身,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。”
1975年宋希濂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,此后他积极投身于两岸交流事业,多次在政协会议上呼吁两岸和平统一。
他在文章中写道:“我亲历了战乱之苦,深知和平统一的可贵,希望台湾同胞能认清形势,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。”
1988年谭政因病逝世,享年82岁。

在他的遗嘱中,特意提到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军事院校,希望能为培养军事人才尽最后一份力。他的藏书后来被收藏在国防大学图书馆,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。
2003年宋希濂在纽约逝世,享年86岁。
临终前他嘱咐子女将自己的骨灰送回大陆,安葬在长沙岳麓山烈士陵园。
他在遗嘱中写道:“我生为中国人,死为中国魂,愿长眠于故土,见证祖国统一。”
陈赓与卢冬生、谭政、宋希濂的故事,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。
他们出身不同、道路各异,却因共同的理想和深厚的情谊紧密相连。
卢冬生用生命诠释了忠诚,谭政用一生践行了信仰,宋希濂在晚年找到了归宿,而陈赓则以他的豁达和重情重义,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。
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,更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缩影,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在民族大义和个人情谊面前的抉择与坚守。
配资平台股票最新消息,正规配资网站,散户配资官网下载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